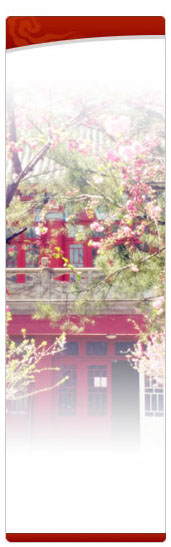“乙巳年九九重阳佳节之际,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党委向全体荣休教师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并组织师生专程走访慰问了我系五位85岁以上的前辈学者。图书馆学教研室助理教授周亚与王翩然带队登门拜访了学界耆宿周文骏教授,向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祝福。”

周文骏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家,自1956年任教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以来,心系学术,笔耕不辍,为系里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而卓越的贡献,在图情学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后学得以拜谒先生,谨聆教诲,感奋激发。故将先生之功业撮述一二,以示学林。
一、周先生文骏其人
1928年1月,周先生出生于浙江金华的一个医生家庭,1948年7月毕业于浙江省立金华中学,并于次年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成为其公开招生的第一期学生。1950年,因家庭经济原因休学,到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院学习俄语,约一年后返回北大复学。1953年毕业于图书馆学专业,并于1956年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从事教学与研究,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84年起任图书馆学情报学系主任、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1990年被国家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图书馆学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三届常务理事,第二、三、四届编译出版委员会主任;中国技术监督情报协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3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规划办“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规划评审组副组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 情报学 档案学》卷图书馆学编委会主任、综论分支主编。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期,曾任国际图联(IFLA)教育和培训专业组常任委员和亚太地区社会情报网络中国顾问组成员。在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主任期间,致力于建立和发展情报学专业。[1]
周先生主要学术贡献在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等研究领域,形成了具有重要影响的文献交流学说,他认为,文献交流工作是图书馆工作、档案工作、书目工作乃至情报资料工作的共同实践特征,指出文献交流学综合了图书馆学、情报学及其关系非常密切的目录学、档案学和文献学的共同内容、原理与方法,对于探究其工作本质和核心矛盾、明确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代表著作有《图书馆工作概要》(1980)、《文献交流引论》(1986)、《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史稿(1949年10月至1979年12月)》(2011)等。[1]

二、因书问道,以学立身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受欧美、日本图书馆学思想之影响,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学如日方升,武昌文华大学等学校先后开设图书馆学课程,图书馆学讲习科、演讲会在全国多所高校遍地开花。先生自幼酷爱读书、嗜喜诗文,至高中时,以“宁静以明志,淡泊以致远”之意,取笔名“淡远”。[2]如此之爱好与性情让他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与书籍生发了一种不解之缘。
1948年从金华一中毕业后,周先生于次年进入王重民先生刚刚创建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学习,成为其公开招收的第一期学生。当时,教师团队包括海外求学归来的顶尖学者如王重民、刘国钧、陈鸿舜、邓衍林、关懿娴、王利器等先生,他们的专业水平、外语能力、研究视野均是一流水准。[2]他们对教学充满热情,关心爱护学生的精神和态度深深影响了年轻时的先生。
在北大沙滩红楼学习期间,先生经常在图书馆自修。王重民教授曾将他在图书馆的办公室钥匙交给学生们,允许他们自由进出。在那里,周先生发现了《国学论文索引》,这份工具书能够集中相关材料,极大地方便了阅读和研究工作,这激发了周先生对图书馆工作的浓厚兴趣。[3]王重民教授批改作业非常认真,通常会附以很长的评语,曾评价先生适合搞图书馆工作和研究,这进一步坚定了他投身图书馆事业的决心;刘国钧教授安排周先生担任俄文编目的助教,并放手让他独立负责一些重要事务,这对周先生的职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3年先生毕业分配。起初被分配到山西太原,后转至临汾,最终落脚曲沃中学任俄语与中国语文教员,同时兼做学校图书馆的工作。然而,王重民教授认为这并非是最佳安排,通过多方沟通,先生得以重返北大,在文学研究所从事具体的采访、编目等一系列图书馆业务工作。
回到北大的周先生并未随文学研究所迁往社科院,而是留在了母校的图书馆学系任教。自此,他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教学与科研生涯,致力于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学等领域的研究。先生曾说:“除了学图书馆学外,我做的全部是图书馆工作。”[3]这句话无疑寄托着他对图书馆事业的深厚情感与执着追求。正是这一时期的经历,使周先生与图书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在此后的岁月里不断探索创新,为推动我国图书馆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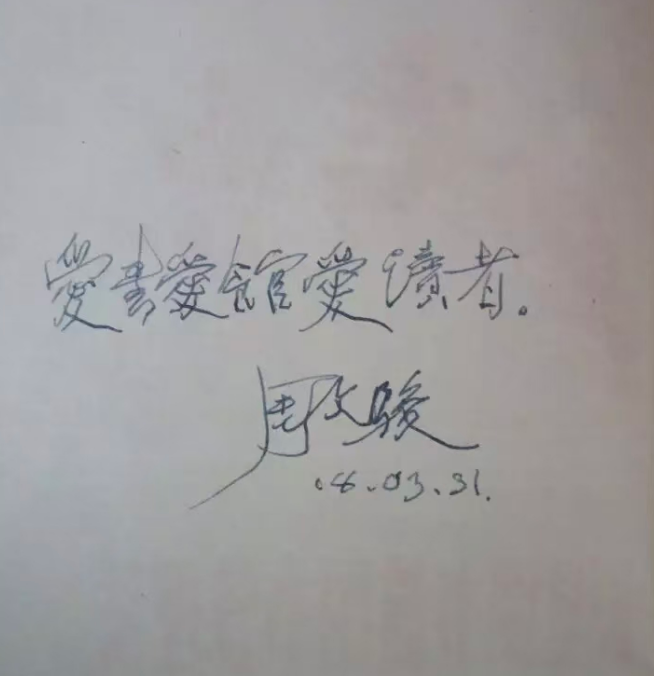
三、立说开新,笔耕不辍
自1956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任教以来,周文骏先生的学术研究始终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探索创新。早在70年代中期,随着科技情报工作与情报学研究的迅速发展,先生意识到了情报学与图书馆学的密切关系,尝试作一些跨学科的探索。[4]在20世纪80年代,先生就任系主任不久,就敏锐地意识到情报学专业独立建制的重要性。他认为,情报学对社会信息的研究主要是研究信息的产生、表述、整序、传播和使用等智能过程和社会过程的原理与普遍规律。这一前瞻性观点理清了情报科学研究范畴,为这一领域未来的探索打好了基础。[5]
1986年,周先生出版了《文献交流引论》一书,正式形成 “文献交流”的思想,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国内外学者给予了高度评价。先生也成为我国图书馆学“文献交流说”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文献交流学是一门研究文献交流全过程的科学。[6]是一种思想交流、知识交流和情报交流。[7]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发展出“大文献学观”,以文献为中心整合与之相关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将其置于统一的文献学体系之下,对其共同本质进行剖析。[8]这种追问本质的系统思维,使得他的理论具有深厚的哲学基础和思辨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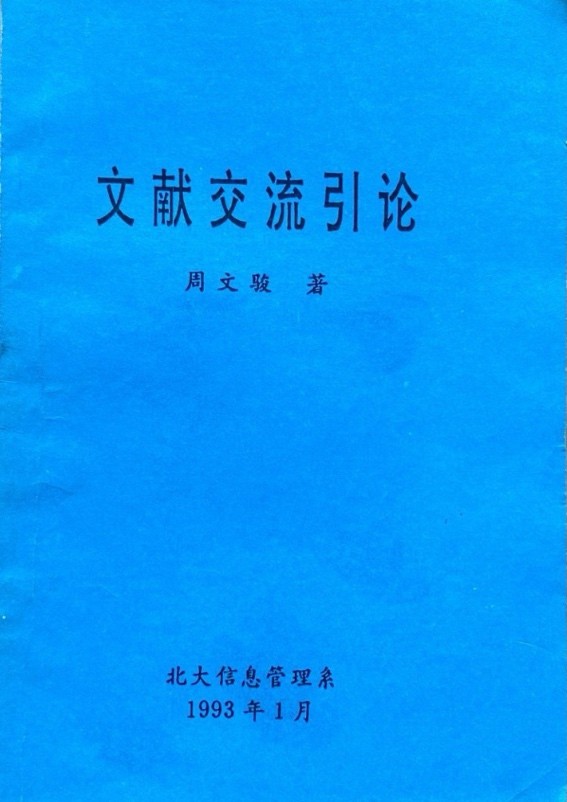
进入90年代后,面对数字图书馆研发和文献资源共享建设高潮,周先生再次投身前沿研究,承担了国家“九五”重点课题“面向21世纪的图书情报工作网络化研究”,并与黄长著、袁名敦主编了《中国图书情报网络化研究》《面向21世纪的中国图书情报工作网络化研究报告》。[8]这些成果为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体现了先生对新技术应用的深刻理解和前瞻性思考。
在耄耋之年,周先生以高度的学术担当,毅然投身于当代图书馆学史这一长期被忽视的领域。为避免图书馆界后学不知晓学科发展史, “重复过去的错误,走相同的弯路”[9],他主动请缨,申报并成功立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中国图书馆学史”。在王红元老师的协助下,历时三年,广览博取,潜心钻研。其研究成果《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史稿》于2011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是我国首部系统反映1949年10月至1979年12月间图书馆学研究与发展的断代史,厘清了学科发展的历史轨迹,揭示了内在规律,总结了经验教训。[9]更因其深刻的洞察力、翔实的史料和纯真的史学品性,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引起了图书馆学界的广泛关注,为当代图书馆事业与学术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借鉴意义。
四、春风化雨,桃李成蹊
作为一名杰出的教育家,周文骏先生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育人理念,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他曾强调,打基础时,导师的作用很重要,读书在精不在多。这种“少而精”的治学方法,帮助许多学生建立了扎实的学术根基。在指导博士研究生的过程中,周先生特别重视激发学生的科研潜力。他鼓励学生们大胆创新,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同时也会在关键时刻给予必要的引导和支持,确保研究方向不偏离正轨。他曾总结出“六个多”——多读、多听、多想、多联系、多总结、多比较。[2]正是在这种严谨而又开放的学术氛围中,他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专业人才,其中不少人已成为了图情领域的杰出学者和海内外诸多图书馆的引领人物。
周先生还十分关心专业刊物的建设与发展。他认为一本好的学术期刊应当具备“观点清晰、材料丰富、参考资料齐全”的文章特点。他还提出建立全国性的图书馆学研究中心,筹办面向全社会的《图书馆报》的构想,希望通过多种渠道促进学术交流与知识共享。[8]这无不体现着周先生对于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全国第四届中青年图书馆学与情报学学术研讨会上,周先生就图书馆学与情报学教育发表了深刻而有洞见的论述,充分肯定了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四十年来的发展成就,同时清醒指出彼时存在的矛盾性问题。为此,他主张从三方面深化改革:一是改进课程内容,比如厘清“概论”类课程定位,强化工具书课程的分层教学;二是优化课程体系,加强基础、合理分流,规范课程边界,融入国际视野;三是推动学科自身向普适性方法科学发展。他还强调教学与科研相辅相成,呼吁理论研究需秉持严谨学风,耐得住寂寞,甘于奉献,服务长远之发展。其观点历久弥新,在三十余年后的今天,仍令人深受启发。

五、暮鼓晨钟,谆谆教诲
半个多世纪的讲台春秋,早已化作未名湖畔最深沉的回响。周先生帮助一代代图情学子筑牢根基,立身所学。乙巳重阳之际,我系师生周亚、王翩然、崔汭、刘宇轩、赵琦轩一行幸得登堂拜访,先生虽近百岁高龄,仍以育人初心对待晚辈后学。
谈及学科发展与青年教师成长,先生鼓励我系师生探索科技前沿,积极应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适宜的项目选择最适宜的工具,多做“工具优化”尝试,提升图情学科学术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在科研道路上,不必拘泥于传统所强调的“厚积薄发”,不要长期积累专业知识却迟迟不见发表成果,导致学术产出稀少。老先生鼓励青年学者,一旦有创新想法,就应勇于探索、大胆尝试,并及时将研究成果付诸发表与实践。
谈及学生成长,周先生提到,学业、生活二者缺一不可,学业上,勿要畏葸不前,有想法便可大胆研究;而在保证学业的前提下,也要充分体验大学生活的丰富,成为内心充盈之北大学子。
最后,先生提及自己对于人工智能这一前沿领域话题的浓厚研究兴趣,然年事渐高,身体抱恙,力不从心,颇为遗憾。还勉励吾辈后学,作为北大的老师和同学,有极佳的环境条件可阅读、可研究、可行走万里,要珍惜现在的条件资源、珍惜青春时光,积极投身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研究与实践,方不负此良辰。《孟子·梁惠王下》有云:“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先生半个多世纪的执教,淡远其名,笃行其道。而今近乎期颐之年,仍心系图情事业之传承与发展,给予我系师生以谆谆教诲。我想,这便是第三代图书馆学人的精神,也是我们北大人回应时代需要的不凡精神。
六、结语
先生生于干戈扰攘之世,然自幼嗜书如命,以“淡远”为笔名,志在宁静致远。及长,负笈北大,受业于王重民、刘国钧诸名师门下,耳濡目染,学问日进,遂与图书馆学结下毕生之缘。自此六十余载,笔耕不辍,著述等身,心系学科,情牵后学,实吾国图书馆学术史之名宿也!
今余有幸拜谒先生,谨聆教诲,见其虽近百年之寿,然精神矍铄,风骨犹存。吾辈后学,躬逢盛世,当以先生为镜,继承其志,弘扬圕学,攀学术之高峰,惟愿薪火相传,庶几不负前辈尊师之厚望也。